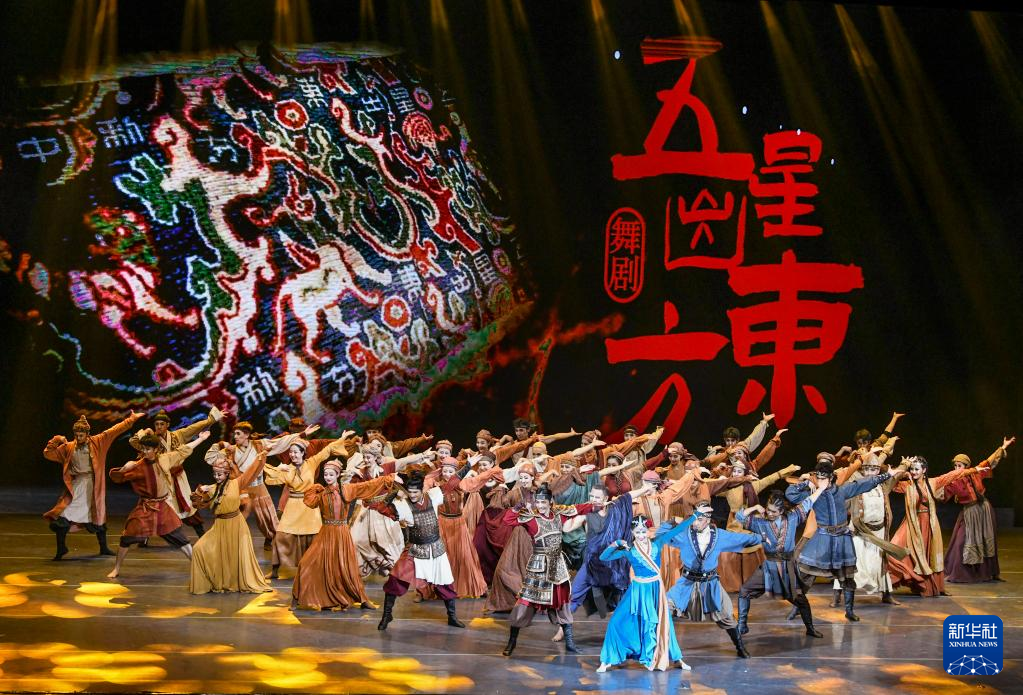□黎蒴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两次陷入固守传统或迎合新变的两难境地。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初,浮躁的情绪造成文坛“嘈杂之声”;到了网络时代,就变成了部落的“悄悄话”。何平在《批评的回归》中是这样描述的:“有很多比传统期刊文学、野文学、网络文学、科幻文学更小的文学部落,甚至单个个体也可以成为一个文学部落。他们利用期刊、书籍等纸质媒体,也利用网络社区、微信官方账号、圈子等。划定边界和领土……”由此,他判断,“我们刚刚进入了一个耳语文学的时代”。文学的这两次转向,是人文价值、资本和互联网技术博弈的结果。当文学的未来变得扑朔迷离时,我们有必要通过认识媒介的作用,重新确立坚守文化价值观的意义。
文学是“人学”,人的社会化本质导致文学创作总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不仅为文学提供内容,也影响着文学领域所有要素的生成,如作家、读者、媒介等。其中,媒介极其重要,它是文学中复杂生产关系的交汇点。文学的基本媒介是语言和文字,或口头或书面,它们赋予文学一种内容形式。但是,文学的“出场”依赖于物质媒介,文字载体从陶器、甲骨、金石学、竹简、绢布到纸张,一路发展到现在的数字媒介。
在接受方式上,文学经历了从听觉形式到视觉形式的转变。听力用的口语文学另当别论,不用说了。文字开始规范文学,然后是文体的划分,短诗、中散文、长篇小说依次出现。造纸容易,能写的字多,意思必然复杂,与思维的复杂是相辅相成的。于是,在某种程度上,社会通过媒介决定文学;根据“媒体即信息”的说法,媒体也创造了相应的社会思维模式。所以印刷时代的文学总是与权威、严肃、高雅、美丽、经典、永恒联系在一起,这是由纸媒的特性决定的。也建立了相应的文学体系,把认同这些风格和兴趣的作家团结到“主流文坛”。
这些现象的背后,是文学标准和审美范式的退化。个人的崛起被视为互联网解放了文学生产力的标志,但这种后果是建立在文学标准丧失的基础上的:不同的人对文学的理解不同,写作能力也不同。以个人为部落写作,使得私人审美取代了支撑主流文坛的审美规范和趣味,个人审美标准超越既定的文学公共标准成为重要的价值取向。标准是要求和约束,也是集体价值观和道德的表达;文学作为人类情感的审美表现,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和审美规范的约束,会忽视社会功能,屈从于人的自然本能。于是,我们看到了新的文学面貌:戏谑、娱乐、消费、低俗等等。
标准的变化在两种风格中最为明显。首先,小说,以故事、传奇、想象为基本特征的网络小说,改变了百年来严肃小说的叙事模式和审美范式。其制造酷点吸引读者的方式,也改变了五四以来文学所坚持的人文价值主张。其次是诗歌,在“文学革命”中,新诗诞生并跃入主流,格律诗被排挤出文坛;在朦胧诗时代,诗歌因为与现实标准不同而越来越流行,纸媒创造并延续了新诗的审美常规。然而,在网络时代,诗歌变成了“私人写作”,既包括坚守纸媒传统的文人写作,也包括大众写作。与此同时,通过对格律诗的革新,大量旧体诗涌现出来。如果小说还是坚持讲故事,诗在节奏之后就消失了,分支就成了唯一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形式,但这个“入”所能达到的标准,大约等于没有。
我们的困惑在于,面对汹涌澎湃的变化,很难说清。对于写作来说,每个人都有写作和发表的权利,文学变得容易,这也许是好事;但对于阅读来说,很难再读“好”的作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变得活跃了,但社会审美水平却降低了。新媒体环境下,阅读与写作互换,文学与社会深度融合。虽然很难做出好坏的二元判断,但常识告诉我们,文学不应该随波逐流。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有了不可改变的文化记忆,个体就可以用归属感来对抗不可控制的现实和命运。谈到“文学”,人们都有自己已经达成相对共识的判断标准,而这个标准是漫长的纸媒时代形成的文化传统,是人文价值的重要体现。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只能回到文学乃至文化与人的关系的轨道上来判断新媒体时代文学的部落化。
作为一种超越文学史经验的力量,新媒体对传统产生了强烈的冲击。然而,无论媒体如何变化,文学仍然应该坚持其文化价值观,仍然是人类的精神家园而不是发泄情绪的“树洞”。文学在适应媒体并不断被媒体再创造的同时,需要坚持其文化属性——这一属性显然构成了评判文学的隐含的、根本的标准。所以,在“窃窃私语”的文学时代,空洞化文学的文化意义,绝对自由的表达或者没有文化基础的写作,终究是出不了好作品的。